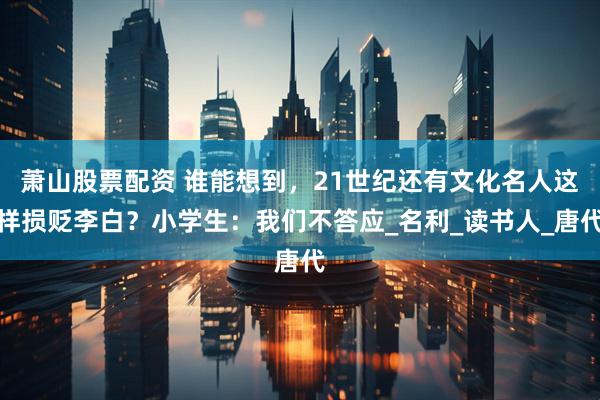
中国拥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长河萧山股票配资,期间涌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文人墨客。这些人物有的以诗词歌赋闻名遐迩,有的则以文章笔法独步天下……无论如何评价和讨论,他们当中的一些名字,始终是绕不开的经典象征。比如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辛弃疾等人,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,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,而非仅仅是某个时代的一个名字。
然而,“人红是非多”这句古训,不仅适用于现代名人,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上的文人。当一些古代诗人被现代人广泛推崇时,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。即便是被誉为“诗仙”的李白,也未能幸免于这种争议。
李白,作为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(在这里笔者宁愿不用“之一”这样的模糊词汇),他的诗作潇洒俊逸,长期以来备受历朝文人推崇。即使到了今天,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,课本中收录了许多他的作品,如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等诗篇早已家喻户晓,成为人们朗朗上口的经典。
当代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李白作出高度评价: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”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李白诗风的豪放与洒脱,也成为现代人对他的普遍印象。
展开剩余74%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对李白如此推崇。著名作家王朔在接受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:“李白是一个求官不成的人……是个名利之徒……”这番话在当今文化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
诚然,说李白是一个“求官不成”的人,并无太大争议,这的确是李白一生的真实写照。李白少年成名,但由于种种原因,未能参加科举考试,因此只能通过多种方式去“求官”。这是一条现实的道路,难以反驳。
为此,李白也曾“献媚逢迎”,在初次见到韩朝宗时,写下了自荐性质的《与韩荆州书》,文中写道: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要知道,在大众印象中,李白通常被描绘成“安能摧眉折臂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不羁形象。因此,当人们读到李白这种“谄媚奉承”的文字时,难免觉得心中那层“光环”破碎,似乎他真成了王朔所说的“名利之徒”。
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
其实,我们要明白古代读书人的根本目标是“学而优则仕”,换言之,读书的终极目的就是做官。古代读书并不像今天这样普及,读书过程中,士子们会被灌输诸如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这样高远的理想,以及“习得文武艺,卖与帝王家”的现实方向。
而要实现这些理想,走上仕途是必经之路。在那个时代背景下,李白作为怀揣壮志的读书人,选择走仕途完全合乎情理。
可能有人会质疑:既然李白想做官,为什么不参加科举,反而要“求官”呢?
实际上,这不能完全怪李白。由于各种原因,他未能参加科举考试,但内心依旧渴望实现抱负,于是便选择了当时盛行的另一条途径——干谒。
“干谒诗文”在唐代非常流行,是读书人通过写诗文向达官显贵推销自己,争取官职的一种常见手段。孟浩然曾为此写下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:“欲济无舟楫,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,徒有羡鱼情。”另一位唐代诗人朱庆馀在科举前也曾拜谒过张籍,写有《近试上张水部》:“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眉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
由此可见,通过干谒诗文“推销”自己,达到求官目的,在唐代并非罕见,且并不丢人。这只是当时读书人为实现抱负,进入仕途的一种正常途径罢了。
李白选择干谒“求官”,并不应该被看作是值得贬损的事情。
而且,从李白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豪情壮志,他的仕途理想并非单纯为了名利。否则,当他被玄宗召见,任翰林时,如果真是为名利所动,早该满足于此。可他因难施展抱负而心生郁闷,常借酒浇愁,直到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仙”,最终被赐金放还。
所以,将李白称为“名利之徒”,显然不公平。
更重要的是,古代读书人追求“名”是很普遍的事,他们所追求的,是无愧于心的名誉,是被历史认可的真名,而非虚浮的名利。
因此,轻易给李白贴上“名利之徒”的标签,实在不妥。毕竟,现代社会中“名利之徒”是一个贬义词,带有强烈负面色彩。
至于王朔对李白的这段评价萧山股票配资,我曾和一些小学生讨论过,结果他们的反应十分一致:我们不同意!
发布于:天津市富华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